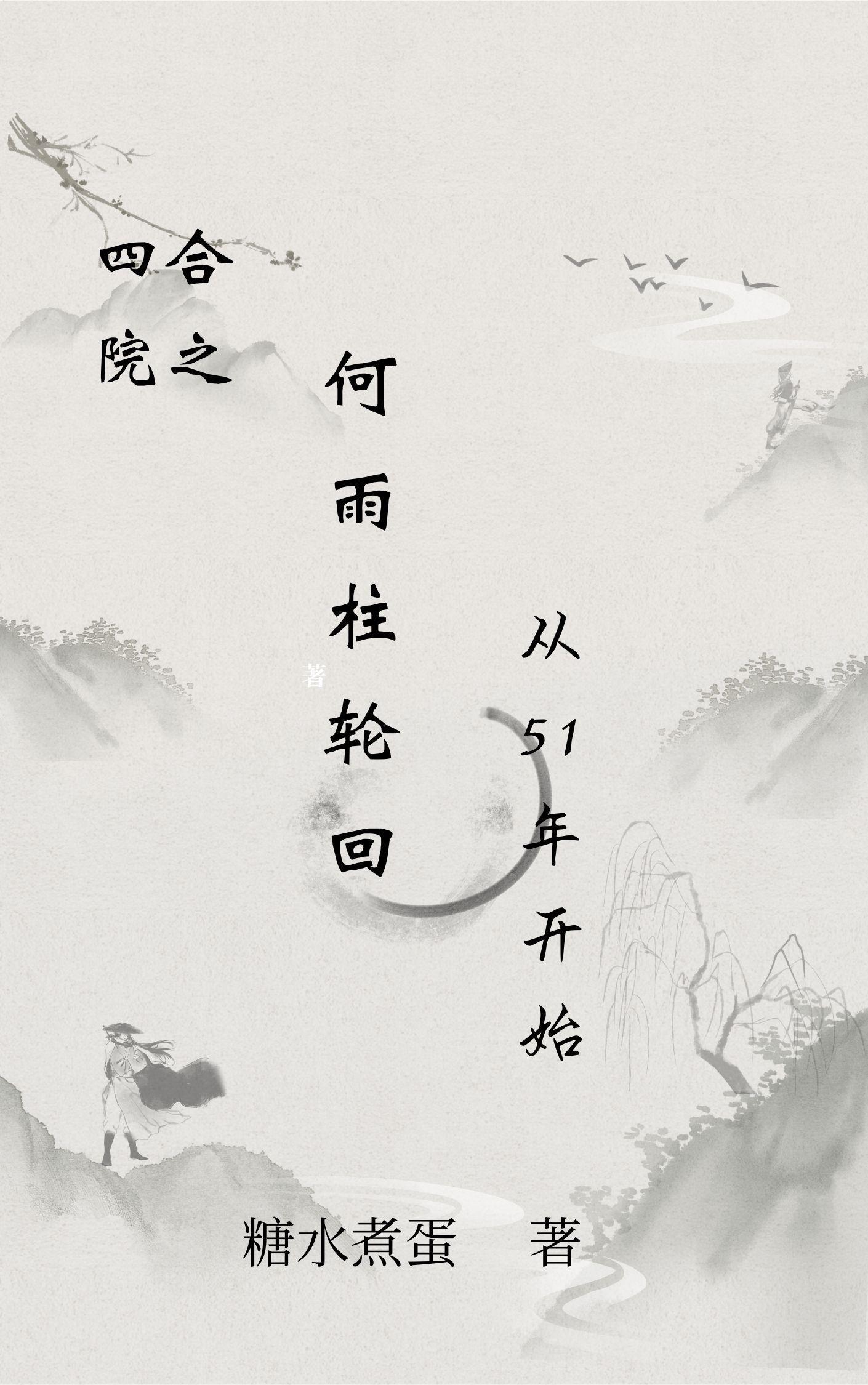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守活寡三年,惨死后重生侯府女配 > 第161章 一念成魔(第1页)
第161章 一念成魔(第1页)
他并非料事如神,知道这宝相寺里生了何事。
而是一连几日,府中嬷嬷往来宝相寺时,却说不曾看到阿若姑娘的身影。
寺中的僧人也都像换了批人似的。
各个望着都眼生。
正巧近日朝中多名重臣联合上奏,请官家重审段家官商勾结案,皇城司的人已经盯了苏家一段时日了。
谁知苏不移行踪诡魅,狡猾至极。
借着暗线的势力,将多年来侵占的不义之财过了多个口袋,将脏银洗得干干净净。
若要彻查,恐怕会牵扯出不少大鱼小虾,京中要不太平了。
官家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,而雍王向来持重稳妥,言行并无失当之处,便委任他协理此事。
今日皇城司的探子来报:“苏不移于寅时三刻带着家奴去了宝相寺。”
赵煦之这才恍然大悟。
他心系阿若的安危,便临时抽调了皇城司的一队人马,直奔宝相寺来了。
把门的假和尚很是凶悍,临死前还刺伤了他的两个护卫,其余贼人也纷纷持刀向前,与他们厮杀到一处。
好不容易闯了进来,却现苏不移已经躺在地上,奄奄一息了。
秋日天气凉爽干燥,火势蔓延得很快,柴房里已是火光滔天了。
“赶紧将里头的人救出来。”
赵煦之从未如此惊慌过,甚至要卷了袖口,亲自冲进去看看,阿若是不是在里头。
可他是官家的三皇子,是雍王殿下,金尊玉贵之躯。
若要有个闪失,无人能负担得起这个责任。
还未向前,便被随行的侍卫拦了下来:“王爷,请三思。”
他们用浸湿的披风拍打着门上的火舌,屋里的人才接二连三地逃了出来,率先出来的是沈夫人。
然后是沈晏清拖着泪干肠断的苏婉容出来了。
她频频回,凄厉地嚎哭着:“父亲,父亲。。。。。。”
沈昱白望了一眼角落里的老太太,本想弃之不顾,可念在那微薄的血脉亲情上还是狠不下那个心。
他亦痛恨自己的心软。
即便后来知道老夫人待檀儿不公,也只是在迫不得已时,用了一颗散元香而已。
他利落地脱掉染血的褙子,轻轻地披在了江檀的髻上,嘱咐道:“火势越来越大了,你先出去等我,冲出去时不要犹豫,仔细被火苗烧到了。”
“二爷为何不跟我一起走。”
江檀反攥住他的手腕,不肯放手。
可顺着对方的目光看去,便知沈昱白是心生恻隐,想将老太太一并救出去。
在这分秒必争的时刻,她也不愿再令其分心,说了句:“我在外面等你。”便缩着身子冲了出去。
见江檀安全逃离了。
沈昱白顿时心安了不少,将模样痴傻的老太太从地上扯了起来,打横抱起。
“呃。。。。。。晏。。。。。。”
她失神地将头侧了过来,才现救她的,并不是宝贝嫡孙沈晏清。
而是她处处都瞧不上眼,甚至企图毒死在娘胎里的沈昱白。
沈老夫人怎能不愧疚?
颤抖着阖上双眼,依偎在沈昱白的怀里。
可瘫痪的人腿脚使不上力,身子也比常人要重上不少。
还未凝固的血液使他脚下一滑,单膝重重地磕在坚硬的石砖上,痛得他咬紧了牙关。
却还是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,从熊熊烈火中得以逃生。
赵煦之望眼欲穿,期冀着阿若姑娘能够安然无恙地从屋子里逃出来。
他抓住沈晏清问道:“里头还有人吗,有没有见到一个姑娘?”
沈晏清这才察觉到,原来姜昙是被雍王安置在了宝相寺,躲着不敢见他。
他不禁开始思考,二人到底是何关系。
难不成见雍王尊贵,姜昙便自甘堕落做了他的暗妾,妄图借此扶摇直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