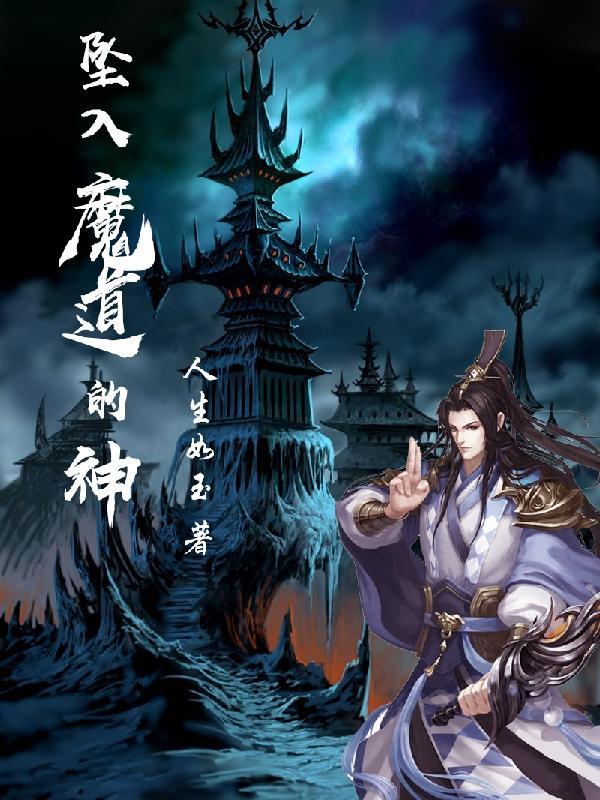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心动过速[破镜重圆] > 第109章(第1页)
第109章(第1页)
她问得坦荡,夹杂着些不谙世事的天真,刘曦路只是冷笑。
“当然看见了。你和商敬言前后脚从包厢里离开,却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了,敢说不是在外面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?”
虽说没什么见不得人的,但被她拒绝总归不是件光彩的事。
看在商敬言曾屡次帮忙的情分上,时鸢有心保护他的隐私,便说道:“那你可误会了。我和商敬言不过是普通朋友,恰好在门外遇见,闲聊了几句而已。”
“普通朋友?”刘曦路复述了一遍,显然并不相信时鸢的话,“他那么护着你,在座的同学哪一个看不出来?”
“先前陈朝予没来的时候,你们两个就暗通款曲,手都拉到一起去了。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,被陈朝予提分手也是活该!”
时鸢本来没想把她的胡言乱语放在心上,可刘曦路这样说,她就忍不住要多问一句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分手了?”
“这有什么难的。”刘曦路脸上闪过得意的神色,“之前班群里聊天的时候,闻妙歌虽然及时撤回,但她口不择言发的那些消息我可是全都看见了。”
她缓缓向前踱了几步,眼神满含讥讽。
“一看就是为你打抱不平、恼羞成怒了呗。哎,不过我也能理解,毕竟被白玩了这么多年,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你应该咽不下这口气吧?”
“真是可怜。”她摇着头,却没有半点惋惜的意思,“由此可见,女孩子还是要自尊自爱的好。”
如果真相正如她所说,时鸢大概也会怒火中烧,但不巧的是,事实与此完全相反,故而她的话落在耳中,只会让时鸢尴尬到想笑。
“那个……其实,分手是我提的。”
然后她就看着刘曦路的脸色迅速变化,像失手打翻的调色盘,精彩极了。
“不可能!”刘曦路厉声尖叫,似乎提高音量就能证明她是对的,“陈朝予那样的条件,你怎么会主动和他提分手?!”
时鸢懒得解释,无谓地耸了耸肩,就见她渐渐镇定下来,编出了一套“完美无缺”的说辞说服自己。
“我知道了,你早就背着陈朝予出轨,害怕事情败露,才抢先提了分手对不对!这样你就可以正大光明脚踏两条船,不用受到道德的约束和良心的谴责!我说的没错吧?”
时鸢被她狗屁不通的逻辑惊呆了,自从开始写文以后,她总是能够轻易发现文章的漏洞,更别说是刘曦路颠三倒四的一番话了。
“心脏的人真是看什么都脏。首先,分手以后接触其他人,不算所谓的‘脚踏两条船’;其次,我是自由的,别妄想拿贞节牌坊那一套来绑架我。”
时鸢顿了顿,无奈摊手:“何况你也看见了,真不是我缠着陈朝予不放。”
硬要说的话,明明是陈朝予阴魂不散地粘着她还差不多。
可刘曦路根本听不进去她的话,一味致力于向她输出。
“陈朝予不过是一时接受不了你的离开,才会对你百般包容。等他完全看清了你的嘴脸,你看他还会不会要你这种人尽可夫的贱货!”
和这种人讲道理毫无意义,多说一句废话,都是对时鸢耐心和智商的侮辱。
眼下刘曦路情绪激动,又自以为占了上风,没有比现在更适合提问的机会了。
时鸢沉下眉眼,不再纠结于与她争执,将话题转到了当年的旧事上。
“高二的时候,我的地理卷子是你偷拿的?”
面对时鸢的质问,刘曦路故作惊讶,可说出的话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
“呀,终于被你这个蠢货发现了。你怎么发现的?让我想想……是不是那天恰好在洗手间里,听到了我们说话,去翻废纸篓了?”
她放声大笑起来:“你也太恶心了吧!”
所以那些话就是故意说给时鸢听的,从始至终都不存在什么意外和巧合,都是刘曦路的精心安排罢了。
“恶心的是你。”时鸢的牙根都在抖,“在学校里恶意造谣中伤我的,也是你?”
“造谣?我可没有造谣。”刘曦路对这个问题却一口否认,“大家都是看到了切实的证据,才发现你纯洁无害的外表之下,竟然藏着如此龌龊不堪的心思……”
“什么证据?”
时鸢迫不及待打断了她,一心想探寻错误发生的源头,刘曦路却不肯如实相告了。
她对此讳莫如深:“你没必要知道。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,证据还在我的手里。”
时鸢深吸一口气,紧握成拳的手背青筋暴起,被攥在掌心的衣角凌乱不堪。
冷静。一定要冷静。
从一开始,她就没指望能够直接撬开刘曦路的嘴。问出这么多信息,已经是意外收获了。
时鸢一边平复心情,一边慢慢问道:“你好像对我……很有敌意?是为什么?”
她脑海中灵光一闪,却又转瞬即逝,让人根本无法抓住。
“你被女德搞得魔怔了?还是……在为陈朝予打抱不平?”
这一次,刘曦路没有立刻回答,无法隐藏的局促与时鸢记忆中的某些细节重合。
是陈朝予忽然出现时她瞬间煞白的脸色,是那些词不达意的搭讪,屡屡落在他身上的眼波。
或许还能追溯到更久远的时候,她尾随陈朝予,闯入了仅有他和时鸢知晓的秘密基地,又在被发现之后落荒而逃。
“我是喜欢他,那又怎么样?”
刘曦路直勾勾地盯着时鸢的眼睛,先前的游刃有余消失不见,取而代之的则是经年累月的执着,其中的疯魔让时鸢顿觉恶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