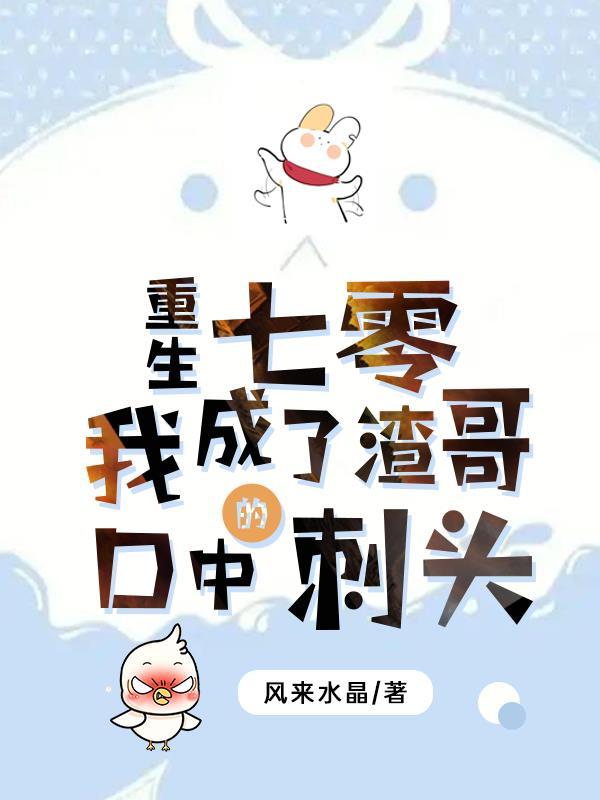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假死后夫君火葬场了+番外 > 第118章(第1页)
第118章(第1页)
说着便替陆怀砚将面纱戴好,陆怀砚的耳侧挂上那两条细链,恍若女子戴了精美的耳饰。
再看陆怀砚戴上面纱后的模样,仔细一看,倒确有几分女子模样。
云梨越看越想笑,最后生生忍住了,不过唇角的弧度和眼里的温度是骗不了人的。
陆怀砚摸摸脸上的面纱,不知道她在笑些什么,虽不明白,但随她高兴就好。
这还是这么久以来,她第一次露出这样真心实意的笑。
陆怀砚兀地出声问云梨,“我戴这个面纱模样很好笑吗!”
云梨咬咬唇,瞬间变得一本正经起来,但再看一眼后,又险些没憋住,而后正色道,“还好。”
陆怀砚,“还好就是挺好笑的,那看来我日后可以多戴戴类似的面纱。”
*
走前,陆怀砚将盖在床板下的一个细长匣子取出来宝贝地揣进怀里,而后才对几人道,“回客栈吧。”
陆怀砚身上是伤,需要人搀扶,那高个黑衣男子搀着陆怀砚下了床,屋内的东西都不要了,也不知三兄弟是从哪个旮沓换来这些东西的。
云梨与吕兰英走在最后,高个黑衣男子扶陆怀砚出去的瞬间,云梨看见陆怀砚后背被血浸染的衣裳,可能是因为有些日子了,那些血迹变成黑红色。
没想到如此爱洁的陆怀砚,也会落得这样一个地步。
几人向客栈走去,为避免引人注意,云梨与吕兰英走在最后,与陆怀砚几人之间隔了很长一段距离。
言聪坐在客栈厅堂里等云梨回来,没想到没等到云梨,竟然等到陆怀砚来了客栈。
看见陆怀砚,言聪腾地一下激动地站起来,双眼似乎隐有泪光闪动,“公子。”
陆怀砚瞥他一眼,朝他点点头,示意他别声张。
言聪随即住了嘴,没再看陆怀砚一眼,无人知晓言聪此刻内心的汹涌澎湃。
天知道这几日他有多担心主子,若主子真有个三长两短,他又有何颜面苟活于世。
不过公子脸上的面纱似乎是云姑娘的。
言聪彻底看不懂了。
陆怀砚对言聪道,“派人备水沐浴。”言聪忙去准备。
而后他又对着兄弟几人道,“此间事已了,届时我写封信,你们回上京时可手握此信前往陆家要奖赏,但切记不可让他人知晓。”
三人闻言,眼里俱是欣喜,这担惊受怕的日子可算熬出头了,日后回到上京,再也不用东躲西藏地过日子了,也不用再做这些冒险之事,以免不小心将自己的小命搭搭上。
过了不久,言聪备好热水命人抬上楼来。
待言聪一看到陆怀砚背后的伤势后,心下一惊,“公子你怎么伤得如此重,可需要属下为公子寻名大夫过来看看。”
陆怀砚目光幽幽到,“不必,顺其自然就好。”
又过了小半个时辰,云梨带回一名大夫来。
她问过言聪陆怀砚住的屋子后,带着大夫来到门边敲响房门,“陆公子,我请了一名大夫来过帮你看看,你若得空,我让大夫进屋来了。”
陆怀砚,“进。”
云梨站在门口没进,对大夫道,“你进去吧,那位公子就在屋内。”
陆怀砚一听,忙缓步来到门口,“你先别急着走,你的面纱还未还你。”
许是陆怀砚刚沐浴完,浑身还散着淡淡的热气,苍白的面容也因此有了些血色,他这幅皮囊的确很好看,饶是看过那么多年,云梨还是会被他惊艳到,但也只是一瞬罢了。
陆怀砚一袭白色寝衣,这些都是他不在时,言聪提前替他安排好的,以备不时之需。
大夫也笑道,“对啊姑娘,你先别急着走,你也可以进屋听听我所说的,这样你才能更好地照顾你夫君,让他快些痊愈。”
云梨解释道,“大夫误会了,我与他不是夫妻。”
大夫了然于胸地笑了笑,没说话。
进屋后,大夫先查看了陆怀砚背后的伤,而后眉头紧紧锁住,“伤得如此之重,怎么拖那么久才看大夫,还有咳嗽,再晚些,恐怕是要入肺腑,身子底子再好,也容不得这样胡乱糟蹋。”
后来大夫又絮絮叨叨说了一堆,一句话,“短时间内好不了,得好生歇息休养,不可过度操心劳累。”
言聪此刻方明白为何主子拦着他不让他去请大夫,原来是认定云姑娘会替他去请大夫来。
大夫叮嘱完后,言聪很有眼色地跟着大夫走出屋去抓药,留云梨与陆怀砚两人在屋中。
言聪走后,云梨站在榻边,凝着榻上安静又虚弱的陆怀砚,声音浅淡道,“陆公子,有什么事待你伤势彻底好了以后再说,你先好好修养吧,一块面纱而已,什么时候还都行,或者直接扔了也没什么,没有其他事的话,我先出去了。”
闻言,陆怀砚掩在衾被底下的手,紧紧握住那块面纱。
见他身负重伤,她什么也不过问,也不在意他为什么而受伤,只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句叮嘱。
陆怀砚想起从前在陆府时,但凡他身子有任何不适,她都会不厌其烦地在他耳旁叮嘱让他当心身子,眼里满是担忧心疼,会亲自煎好药端来给他喝。
那时他并不在意她为他做的这些,总觉得她那些不过是她装装样子,做给她自己、做给旁人看的,别有用心而已。
若汤药太苦,她还会用哄孩童的语气柔声哄他,会趁他不注意往他嘴里放进一颗饴糖。
他不喜甜,他还记得那日他因此事对她发了好大的火,自此以后她再也没这样做过,只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他,不敢再做出任何他不喜欢的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