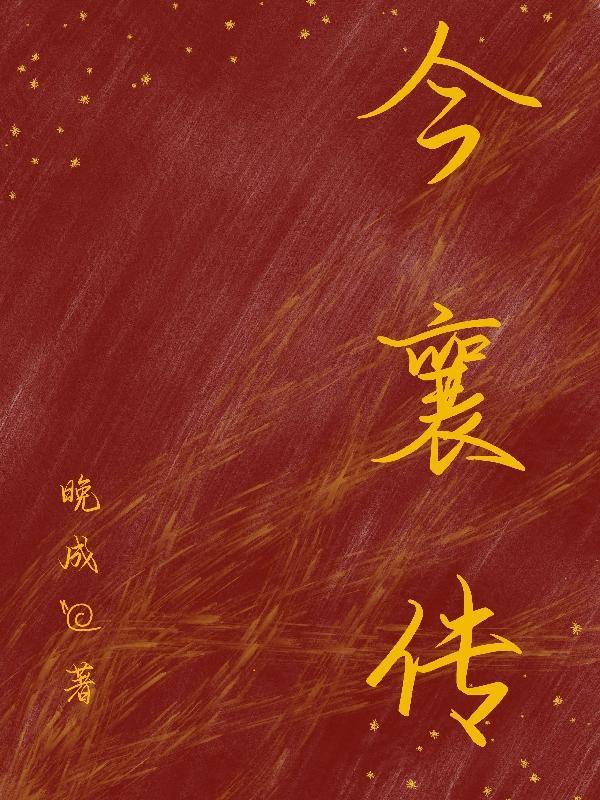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序列大明 > 第681章 不赖足矣(第2页)
第681章 不赖足矣(第2页)
「您都不知道,那时候我过的能有多惨。别说什麽山珍海味了,就是原生的米面油蛋,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。连农序那些黑心老农不知道怎麽炮制出来的合成垃圾,我都能吃的喷香。吃完了还舍不得扔,得装上水备着,说不定什麽时候还能拿出来吸溜两口。」
「有时候真饿的受不了,我就只能去偷去抢。趁人不备,一个飞身扑上去,抓住吃的就往嘴里塞。然后就地一倒,两只手把头一抱,任由别人拳打脚踢。偶尔运气不好,被人一脚踹中肚子,那别说今天的饭,就连昨天的都得吐出来,只能白白挨一顿打。」
「所以您说,儒序六艺我学哪门?当然只会学『射』艺了。在我看来,枪弩可比嘴巴会讲道理,谁要是不听,我就一枪打爆他的头,人死了也就老实了。」
张嗣源话音滔滔不绝,像是打算一股脑将肚子里面的苦水全倒出来。
此时,地面上还在不断响着渡世救人的道法。
高处的风却卷着满是人世苦涩的话,不知道吹往何方。
「这些年为了活下去,我做过劳工,当过摊贩,混过帮派,干过戍卫。老话说这世上足足有三百六十行,可是我当时能看到的路,不过只有几条狭窄逼仄的崎岖小道。
「就算是这样,前面都还堵着茫茫多的人,跟在后面的也在不断奋力推攘,我就这样被挤在中间,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。」
「不过,我也不是没过过好日子。」
张嗣源一脸缅怀,砸了砸嘴唇道:「我觉得过的最安逸的那几年,是在南直吏一座偏远小城里的夫子庙当洒扫庙仆。事儿不多,还管三餐,白天跟着『之乎者也』摇头晃脑,晚上就偷偷溜进夫子庙的黄粱梦境。」
「那时候我就觉得,嘿,这黄粱梦境还真他妈的好,想要啥都能有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,就是梦醒的时候冷飕飕的,要在被窝里上半个时辰的呆,才能把身子暖和过来。」
张嗣源梗着脖子,大声嚷嚷道:「裴叔您说句公道话,这天底下有这麽给人当爹的吗?」
「老头子确实不是个东西,光顾着自己吃香喝辣,却让自己的崽儿颠沛流离。要我说就该锁了他的记忆,封了他的能力,把他也扔进这世道里,好好尝一尝人情冷暖,世态炎凉!」
裴行俭嘴上恶狠狠的骂着,眼中却带着淡淡笑意。
「倒也不至于这麽严重。我皮糙肉厚,吃点苦没什麽。他年纪都那麽大了,哪儿经得起这麽折腾。」
张嗣源讪笑着挠了挠头,抬眼望着头顶暗无星辰的深邃夜空。
「说恨,确实恨。我以前总想着要是哪天混好了,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这老东西,当着他的面痛骂上个三天三夜。他要是还有其他的儿子,那就更好了,我一定会亲手把他们的手脚掰断,以泄心头之恨。」
张嗣源两眼放空,喃喃道:「可真当我找回记忆和身份之后,却忽然现自己其实没那麽恨了,因为我明白他为什麽要这麽做。也知道他吃的苦受的累,虽然跟我不一样,却比我还要更多。」
「最多就是有时候会扇自己一耳巴子,骂一句为什麽非要这麽懂事?难道真就当惯了逆来顺受的穷苦人,连一个耍性子的纨絝子弟都不会当了?」
「除此之外,就是有时候会觉得纳闷,自己的记忆好像莫名其妙缺了一块。」
张嗣源转头看向裴行俭,「您说,老头子要真是从小就把我扔出来,那么小的崽子到底怎麽活下来的?为什麽在我的回忆里,自己好像从一开始就是个半大小子?」
裴行俭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,打趣道:「所以你小子絮絮叨叨说了这麽多,就是想从老夫的嘴里知道你都忘了什麽,对吧?」
「您给我说说吧,是好是坏都无所谓,我只是不想自己总是忘了点啥。」
裴行俭心里明白,其实张嗣源心里或许早就有所猜测。
只是多年的漂泊让他没有自信,生怕事实并不是自己预想的那般。
可若是不问,却又总是如鲠在喉,念念难忘。
「你确实从小就离开了京城里的那个家。」
裴行俭话音顿了顿:「不过在你十二岁之前,是你爹牵着你的手陪你走了大半个帝国。不过他并没有为你解开这段记忆,或许是因为他人家不想你的人生里有太多他的影子。」
「这老头一天就是想法太多。俗话说得好,上阵父子兵,他要真想绝天地通,我理所应当为他牵马坠蹬。兜了这麽大一圈,我现在还不是做着同样的事情?」
「不一样。」
裴行俭轻轻摇头:「并肩并不一定就代表同道。你有你自己的想法和理念,你现在做这些事,是因为在你心里孝比理大。可等我们这些人都尘埃落定,你总有一天也会为了自己的理念破浪前行。」
「你如今还是老师的儿子,但到了那时候,你就只是张嗣源,懂吗?」
「嗯,我都懂。」
张嗣源埋着头,让人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。
「不过裴叔。这老头给我当爹,其实当的还算不赖,对吧?」
裴行俭重重点头,大笑道:「老师如果能听到这句话,一定会更开心!」
咚!
弋阳城中回荡起悠扬的钟声,宣告又是一夜子时已到。
从高楼看去,街道中涌现出密密麻麻,不过指头大小的人影,彼此摩肩接踵,朝着位于城中央的弋阳道宫而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