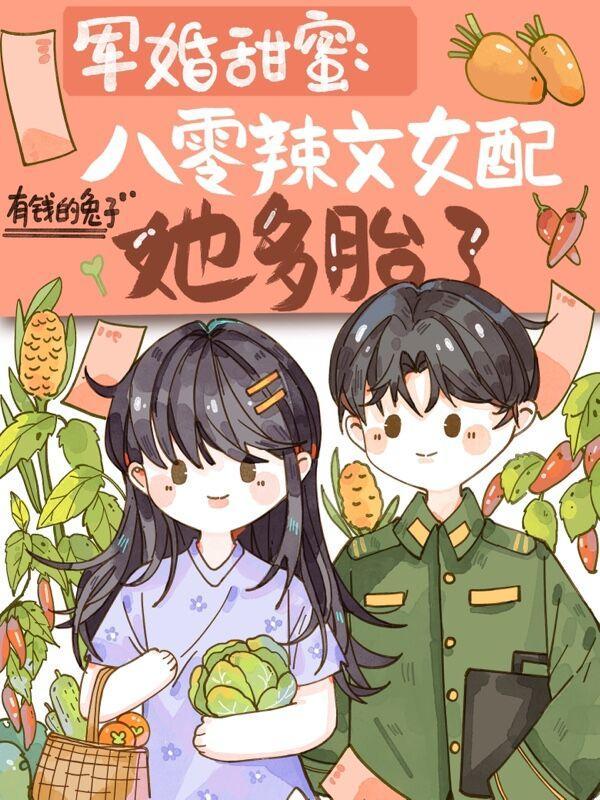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皇妃升职手册 > 第683章 朕一个字都不信(第1页)
第683章 朕一个字都不信(第1页)
当梁王将这封信拿给魏德善看时,魏德善难以置信,他坚称这封信的确是信郡王写给他的,他将信藏起来,正是担心有朝一日事迹败露,也好有个说道,但现在这封信竟然是空白的,简直匪夷所思,
“这封信肯定有问题,如若真是空的,我又何必告诉你们信封的位置,让你们去翻找?那岂不是白折腾一场?”
魏德善所言在理,但这封信的确是空的,另一位官员吴大人不禁猜测,这是不是特殊处理过的信,兴许用火烤可以显现字迹,于是梁王吩咐下人将信放在火烛之上,离得远一些,小心烘烤。
可试了半晌,仍旧没见上面显现一个字,他们又试了淋水之法,依旧未果,看来这信是真的没有字。
如此一来,魏德善所谓的证据便没了,他没有其他的东西能证明信郡王与他暗中来往。
独有一人可证明,便是宁王,可他马上就要被斩,他的家人还需要宁王照看,他哪敢将宁王卷进来?再说他与宁王只是口头约定,并无实证,这话说出来也没人信。
魏德善的证词没了用处,他拿不出证据来,那么信郡王的罪名也就无法成立。
宗人府将此事上报给皇帝,章彦成只觉怪异,他看着宫人呈上来的那封信,暗自琢磨着,“一个将死之人,没道理撒谎才对,为何那信上没字呢?”
明兆也在这儿,他看着那封信,灵光一闪,不禁想到了某种可能,“听闻有一种特殊的墨水,写过字之后,过不了多久就会逐渐消失,信郡王很可能是防着魏德善保存这封信,所以写信时用了特殊的墨水。魏德善自以为有证据在手,殊不知,那信上的字迹早就消了。”
“那可有法子将字迹还原?”
听闻父王什么法子都试了,那就证明没戏了,“有些字是可以还原的,但特殊的墨水无法还原。只能说信郡王太狡猾,怕留把柄,便提早留了这一手。”
这不是章彦成想要的结果,他以为有了魏德善的供词,就能定章彦安的罪,却没料到章彦安竟还藏了一手,
“难道这线索就这么断掉了?就没有其他证据指控他?”
明兆无奈摇,“我父王那边只查到这么多,目前看来,魏德善的证词毫无用处,只怕难定章彦安的罪。”
心有不甘的章彦成不愿就此放弃,“朕就不信他做事如此缜密,居然没有留下一点儿蛛丝马迹?传朕旨意,继续探查!”
吴大学士在听闻皇上的指令后,格外为难,他向梁王求助,询问梁王的意思,梁王只道此事他不必再管,梁王会入宫一趟,亲自跟皇帝商讨。
皇帝要查,梁王便秉公查办,可查了几日却没有实证,梁王便不愿再继续,
“皇上,魏德善之言不可尽信,于连海和他勾结尚有证据,但说信郡王与他勾结,并无实证,兴许他只是想挑拨你们兄弟之间的关系。”
此事疑点重重,那便有查证的必要,“魏德善怎会摆一封没有字的信在暗格之中?皇叔不觉得那封无字信很可疑吗?这事儿得继续查,尚未出结果,皇叔无需着急下定论。”
“那要查到何时?一直没证据便一直将信郡王关在宗人府吗?臣民们可都在看着呢!他们会私底下议论的。”
梁王的态度不禁令章彦成起了疑,“这才三日而已,皇叔你急什么?你就认定信郡王无罪吗?”
梁王之所以这么说,自有他的道理,“不是臣认定他无罪,而是魏德善给不出实证,单凭他一句话,无法给信郡王定罪,魏德善的死期已经到了,这事儿不了结,魏德善也杀不得,一拖再拖终究不是什么好事。所以臣的意思是,既然没有实证,那就放了信郡王,以免朝野上下议论纷纷。”
章彦成眸眼微眯,状似无意地随口问了句,“哦?他们在议论什么?”
迟疑片刻,梁王才道:“那些臣民都在传,说前太子已经被圈禁,如今您又要对自己的另一个亲兄弟下手,是要斩草除根,除掉所有对你的皇位有威胁之人。”
“简直荒谬!”章彦成怒拍桌案,“大皇兄被圈禁是父皇之令,是他咎由自取,并非朕要圈禁他,至于信郡王,他私自与魏德善勾结,分明是要走大皇兄的老路,朕不能因为他是亲兄弟就姑息,他敢做,朕就敢查!”
“先帝已去,于连海已然伏法,篡改先帝遗愿一事,信郡王并不知情,他只是被于连海推到了台面上而已。他和魏德善并未勾结,只是当时他以为那遗诏是真的,以为自己真的是继承人,才会下令让魏德善动武,这些都是于连海闹出来的,信郡王是无辜的。”
听着梁王的分析,章彦成忽然觉得,派梁王去查此事是个错误的选择,“皇叔您所说的这些,难道就不是信郡王的一面之词吗?他说不知情,您便信了,您这耳根子未免太软了些。”
梁王自认公正,并未偏袒,“臣不会偏信谁的话,只会根据事实去判断。”
事实就是章彦安他蠢蠢欲动,“皇叔您可能不知道吧!早在父皇还在世时,信郡王就曾多次暗中与宁王来往,而魏德善正是宁王妃的亲眷,他们勾结之事,朕早已察觉,所以他的话,朕一个字都不信!”
“所以皇上您打算怎么查?查信郡王,查宁王,把您的兄弟叔叔都给定罪吗?天下人会怎么想?会认为您才登基就开始打压皇亲,排除异己!”
章彦成眉心微跳,他本就满腹怒火,梁王之言一如火上浇油,烧得他双目通红,扬声怒斥,
“若非他们暗中勾结,心怀不轨,朕又怎会去查?做错事的是他们,皇叔您不去指责他们,竟然怪朕查得太严?”
明知皇帝动了怒,梁王仍旧不妥协,依旧坚持己见,“所谓的勾结造反只是您的臆测,并无实证,于连海都说自己没有勾结信郡王,只是觉得信郡王宽仁,为了自己的利益,才想扶他上位而已。
先帝患病是突状况,于连海临时起意,当时信郡王并不在场,他们并没有商议的机会。”
章彦成放在膝间的手缓缓蹙起,龙袍逐渐泛起褶皱,威严的龙头忽而变得狰狞,“信郡王宽仁,朕就暴虐吗?”
察觉到失言,梁王镇定拱手解释道:
“臣并非此意,只是在转达于连海的话。臣这番话或许不中听,但臣绝无私心,皆是出于对朝局的考量。
像彦州那般证据确凿的,如何处罚皆可,然而信郡王之事不同,现下只有魏德善的供词,没有实证,您不该就此武断下定论,臣只是不希望皇上您被天下人诟病,这才斗胆进言,还请皇上三思!”
关于此事,章彦成问心无愧,“朕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,朕可没有冤枉任何人!”
皇帝认为自己没有错,梁王身为旁观者,冒着被皇帝嫌恶的风险,也要直言进谏,
“皇上,你要查于连海,势必会牵扯到其他官员,牵动整个朝局,有些事,不破不立,这也是先帝的心愿,你能有这份决心,改革弊政,先帝也很欣慰,但凡事不能做得太绝,得适可而止。
此次的事,朝臣私下里肯定会议论纷纷,皇上您若再动宗室,那皇亲国戚们更会有微辞,对你很不利。眼下正是应付盛国的紧要关头,可不能出什么内乱,依我看,要不就先整顿官吏,至于宗室们,缓一缓再说。”
起初章彦成还试图与梁王讲道理,但几个回合下来,他突然明白了,梁王是不论道理的,梁王的意思再明显不过,不论章彦安是不是与魏德善有勾结,这事儿都不该再查下去,总而言之一句话,梁王想要息事宁人。
“皇叔,在朕的印象中,你可是刚正不阿的,如今你怎能不顾事实,明知此事有蹊跷,却要和稀泥,这是什么道理?”
“因为我知道,亲情比真相更重要!”梁王神情黯然,慨叹道:
“先帝骤然离世,臣委实难接受,比起性命亲情,权势又算得了什么呢?社稷安稳才是最重要的,臣恳请皇上顾念大局,莫再追究此事,就此作罢,也好全了兄弟之情,不给旁人留话柄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,皇上您开恩给信郡王一个机会,料想他定会感恩戴德,以己之力,报效家国。”
梁王再三劝诫,章彦成既未拒绝,也未答应,只道此事关系重大,需慎重考虑之后再做决定。
晚间回到撷芳殿用膳时,章彦成闷不作声,以往他可是很爱说话的,会主动跟瑾娴讲一些趣事,今日他沉着脸,若有所思,瑾娴便觉他不对劲。
正走神的章彦成忽见碗中多了一块红烧肉,这才抬眸望向瑾娴,“看来你今日心情不错,居然会主动给我夹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