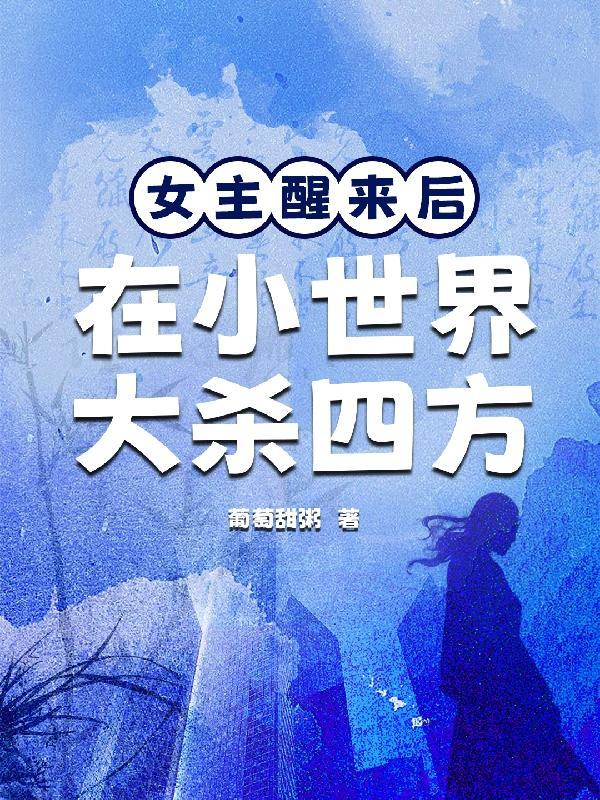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暮染夕沉[先婚后爱] > 第29章(第2页)
第29章(第2页)
旋转门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样子,她亲手种下的绿植被刀砍倒,残枝满地,就连前不久修缮的烫金牌匾也被人用石头砸下,印满了杂乱的鞋印。
入目不堪,一片狼藉。
而事发的始作俑者,正穿着一身皮马褂,坐在前台唯一没被砸坏的高椅上,有一下没一下的踢着脚边的青瓷碎片。
举手抬足间,恶意尽显,先前那般儒雅商人的模样他甚至都不愿意再装。
他其实很清楚,顾佑远是他不敢惹的人物,他的隐婚对象曝光后,连带着沈暮帘这个黄毛丫头他也不敢招惹。
自从沈氏被收购在沈暮帘麾下,他再也捞不到油水,愤恨已久,只是一直顾忌顾佑远才没有出手,如今仔细打探才知道,顾佑远因公事滞留在布达佩斯,按照事情的棘手程度,没有两个月压根回不到坞港。
几乎是一瞬间,他心中的孽苗腾出了芽尖。
他早已订好了后天离开坞港的船票,也顾不得这究竟有多铤而走险,只要再从沈暮帘这捞最后一笔,也够他下半辈子富余。
顾佑远再有本事,还能为了一个女人逼他到天涯海角么?
想到这,他哼笑一声,扭头看向伫立在门边的沈暮帘,稍稍愣了愣。
印象中,沈暮帘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,十指不沾阳春水,被沈陇捧在手心,做事向来莽撞,要是以往的她,早就冲上前来掐着他的领结歇斯底里,质问为什么要这样。
可她的反应与他想象中截然不同。
如今站在他面前的沈暮帘,冷静镇定得让他渗出寒意,那双透彻的双眼甚至找不到一丝怒意,却有几分他看不清的星点,参杂在里面。
看到这幅景象,沈暮帘无波无澜,仿佛面前不过是一场天亮就醒的幻象,轻巧越过脚下坠落的水晶灯,一步步逼近椅子上厚颜无耻的中年男人。
明明她的身形十分单薄,可舅舅却能在她身上看到不可言喻的压迫,这种压迫仿若乌云,正层层向他压过来。
他在这种气势下不禁后仰半步,目光有些焦灼的飘忽,在她站定之前,抢先一步扬声:“给我五千万,我保证不会再来闹事。”
本以为沈暮帘还会怒斥他狮子大开口,没想到她只是扬了扬眉,弯下腰在柜台下找了个卡灵杯,轻巧应声:
“行。”
舅舅懵了片刻,像是想不到竟然这么顺利,油腻脸上刚要露出贪心的笑,便听见她在倒水的间隙缓声说出条件:
“说出谋害我父亲的凶手,这些钱我会一分不差的打在你的账户上。”
他一愣,眉心猛的皱起:“你怎么还在想这个?”
开水注入杯中的气泡缓缓浮起,沈暮帘在他浓重的疑问声中,抬起眸,平静的望着他。
他却在这寡淡的一眼中仿佛看见了猛烈的惊涛骇浪,铺天盖地的心虚倏地袭来。
“我……我什么都不知道,你父亲都死了六年了,当年也是断定是意外,”他垂下头,不安的咽了口唾沫,“你问我我怎么……”
他语无伦次的辩解,蓦地被空中一声微不可查的叹息打断。
他的呼吸猛地顿住,耳边骤然掠过沈暮帘清润的嗓音。
“舅舅。”
她摩挲着杯沿,感受热气逐渐在指尖凝成水珠。
“我也给过你机会了。”
舅舅心下一震,倏地抬眼,电光火石间,烈阳折射在高举的卡灵杯上,晃得他瞳孔生疼,他下意识想要抬手遮光,手掌却蓦地被人摁在写字台,玻璃的碎裂声响起的下一秒,利刃刺入肉体的尖锐疼痛便猛的袭来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