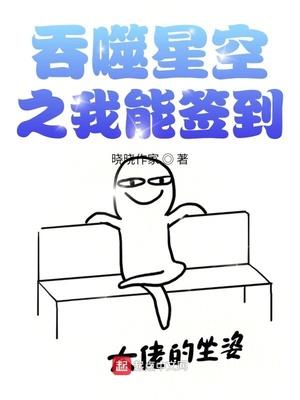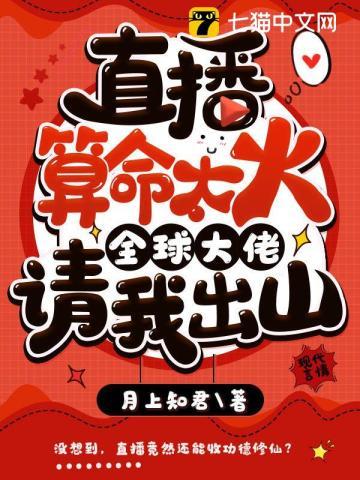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女侠叶沛 > 第三章 情窦初开女儿心事无人知(第3页)
第三章 情窦初开女儿心事无人知(第3页)
“谁啊?”
楼子衿的声音传进来:“你洗完澡出来吃烤芋头吧,我烤好了,院子里等你。”
“知道啦。”叶沛几乎要笑出声来,她强忍着,从水里钻出来。擦干身体,穿上衣服,将头发松松地绾上。
厨房门开着,楼子衿坐在灶台旁盯着炉火。见叶沛出来了招呼她说:“坐到这里来吧,院子里还是有点凉,等你头发干了咱们可以坐到房顶上去纳凉看星星。”说着顺手把一个刚烤好的芋头递给叶沛。
叶沛接过芋头,说:“咱们现在就去屋顶上吧,我不冷,炉旁太热了。”
“你要是不冷咱们现在就去,等我把炉火熄了。”等他收拾停当,二人出了厨房。
楼子衿走到自己房前的大树下,右脚点地,左脚登树干,手已经抓住高枝,再一用力,轻松地翻上了房檐。叶沛用同样的方法跳上房,楼子衿伸手拉着她,坐在屋脊上。
叶沛攀着楼子衿的胳膊,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,楼子衿包好了芋头递到叶沛手中,自己也包一个慢慢地吃起来。
“今天有点云彩,好像月色不明。”楼子衿望着天空说。
“我觉得今天的星空是最美的
。”叶沛甜蜜地笑着。
楼子衿感叹道:“如果一辈子都可以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该有多好啊?”
叶沛说:“这有何难?只要你不离开,我也不会离开师父,咱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!”
楼子衿突然有种莫名的感动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他搂过叶沛的肩膀,让她紧紧地挨近自己。而叶沛没有察觉楼子衿的异样,此刻她只是觉得甜蜜、温暖和安慰。
就在这无尽的夜色里,两个人相互依偎,也不再言语,默默地吃着芋头,看着星空。
安常起夜从茅厕出来,看见了屋顶上坐着的两个人,如同金童玉女般相配,他会意地笑笑,继续回屋睡觉去了。
第二天叶沛睡了一个懒觉,不知道是不是昨夜吹了冷风,她觉得浑身酸痛,小腹尤其胀痛。她懒懒地起身,看见床上竟然有一滩血,吓得差点惊呼出来。她觉得眼前眩晕,又怕又惊,瘫坐在床上。
经历了灭门惨案,叶沛对血有着深深的忌讳或者说心理阴影,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,感觉死亡逼近了她。
正在这时,楼子衿过来看看叶沛为何这时还未起床,他不见外地轻敲了两下门就推门而入,一边说着:“师妹,你今天怎么这时还没起床,可不是昨夜吹了冷风着了风寒吧?”
进门见叶沛瘫卧在床上十分奇怪:“师妹?你怎么了?果真不舒服?”楼子衿走近,见叶沛面色苍白,轻轻摇晃她说:
“师妹?”
楼子衿猛然发现床上的一摊血迹,大惊。“师妹,师妹,你怎么了?昨天不是还好好的?”
叶沛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,她觉得自己好像就要死了,她再也看不见眼前这个她喜欢的人了。
楼子衿急道:“你别怕,我去叫师父!”说着,他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屋。
巴山和安常正在屋里商量采买精铁的事情,见楼子衿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道:“师父,您快去看看,叶沛,叶沛也不知怎么了,流了好多血!”
巴山听了也吓一跳,放下手中的本子赶紧往叶沛的房间走,安常紧跟在他身后。
巴山进屋见到叶沛的状态,似乎明白了什么,安慰道:“你先别怕,师父来看看。”说着为叶沛把了把脉。
安常跟进来看到这情形,对巴山说:“葵水?”
巴山会意地点头说道:“应该是。”
安常笑起来。
巴山放下叶沛的手腕也平静地安慰她说:“没事,孩子,别怕,没事的。”
楼子衿坐到床头,搂着叶沛安慰,他见师父和安常的表情后奇怪地问:“到底是什么病?”
安常笑道:“是女孩子的病。”
楼子衿更加不解。
“癸水?”叶沛猛然想起小时候听母亲和乳母提起过这个词,顿时羞得满脸通红。
安常对巴山说:“不如送她到神山道长那去住几天吧?”
巴山说:“也好。”
楼子衿不安地问道:“师父也治不好她吗?为什么要去别处?”
安
常说:“她没事。”
巴山也安慰道:“你放心吧!叶沛没事的。”
楼子衿不放心地搂着叶沛,心想,没事怎么会流这么多血?可是师父说没事他又不好深问。
他摸摸叶沛的额头,确实滚烫,更加不放心,安慰道:“好妹妹,你别怕,我在这儿呢!”
虽然楼子衿强烈要求要去送叶沛,巴山、安常、甚至叶沛自己都拒绝了,他只好不放心地目送安常和叶沛走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