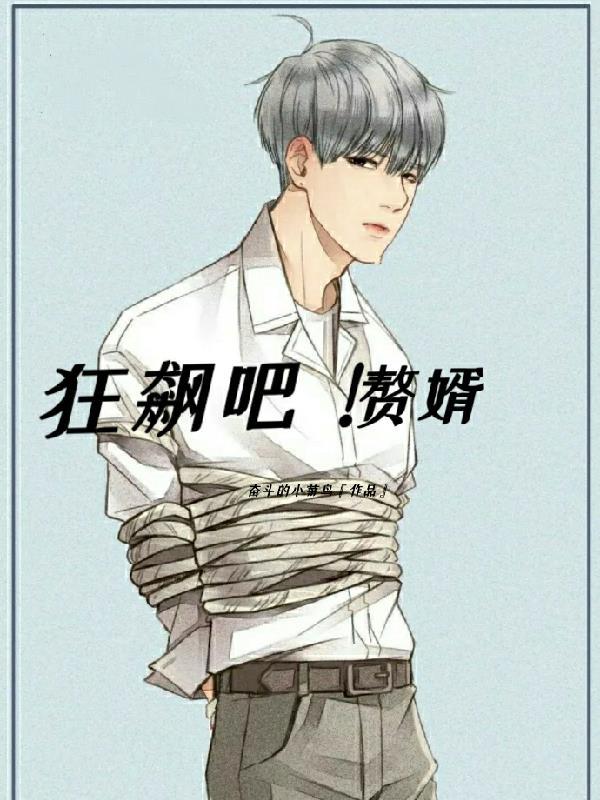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皇后卷哭了整个后宫 > 第79章 这男人有毒(第2页)
第79章 这男人有毒(第2页)
念蝶正掏腰牌的手一顿,她心惊地看着面前突然变脸的男人,颤着唇道:“大人,奴婢怎么敢开罪大人,可这腰牌……”
“既拿了,就好好收着。”
念蝶垂头,手握紧,一字一句说道:“但奴婢不会……不会……委身于大人。”
付黄贺忽然抬起握在剑上的那只手,朝她的头顶揉了一下,念蝶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,一下子僵硬在那里。
她抬头,怔怔的看着付黄贺,付黄贺没看她,从她手中又抽走那封信,转身就走。
念蝶听见他笑着骂了一句:“傻样,你想委身于本将,想上本将的床,还太早了。”
念蝶:“……”
都说了谁想委身给你了,谁想上你的床了,啊啊啊啊啊,这男人有毒吧!
念蝶回过神,连跑好几步路,喊道:“大人,信是送给宁家的!”
付黄贺已经走出去很远很远了,念蝶不确定他听没听见,还想再喊一声,看到越来越远的男人冲她挥了一下手。
应该是听见了。
念蝶松一口气,怔然的站了片刻,转身朝凤罗宫走。
这一路上她心事重重,回去后实在拿不定主意,就找燕宁,将那个腰牌拿了出来,说了如何得到这块腰牌的前因后果,也把刚刚付黄贺握她手的事情说了。
念蝶正掏腰牌的手一顿,她心惊地看着面前突然变脸的男人,颤着唇道:“大人,奴婢怎么敢开罪大人,可这腰牌……”
“既拿了,就好好收着。”
念蝶垂头,手握紧,一字一句说道:“但奴婢不会……不会……委身于大人。”
付黄贺忽然抬起握在剑上的那只手,朝她的头顶揉了一下,念蝶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,一下子僵硬在那里。
她抬头,怔怔的看着付黄贺,付黄贺没看她,从她手中又抽走那封信,转身就走。
念蝶听见他笑着骂了一句:“傻样,你想委身于本将,想上本将的床,还太早了。”
念蝶:“……”
都说了谁想委身给你了,谁想上你的床了,啊啊啊啊啊,这男人有毒吧!
念蝶回过神,连跑好几步路,喊道:“大人,信是送给宁家的!”
付黄贺已经走出去很远很远了,念蝶不确定他听没听见,还想再喊一声,看到越来越远的男人冲她挥了一下手。
应该是听见了。
念蝶松一口气,怔然的站了片刻,转身朝凤罗宫走。
这一路上她心事重重,回去后实在拿不定主意,就找燕宁,将那个腰牌拿了出来,说了如何得到这块腰牌的前因后果,也把刚刚付黄贺握她手的事情说了。
念蝶正掏腰牌的手一顿,她心惊地看着面前突然变脸的男人,颤着唇道:“大人,奴婢怎么敢开罪大人,可这腰牌……”
“既拿了,就好好收着。”
念蝶垂头,手握紧,一字一句说道:“但奴婢不会……不会……委身于大人。”
付黄贺忽然抬起握在剑上的那只手,朝她的头顶揉了一下,念蝶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,一下子僵硬在那里。
她抬头,怔怔的看着付黄贺,付黄贺没看她,从她手中又抽走那封信,转身就走。
念蝶听见他笑着骂了一句:“傻样,你想委身于本将,想上本将的床,还太早了。”
念蝶:“……”
都说了谁想委身给你了,谁想上你的床了,啊啊啊啊啊,这男人有毒吧!
念蝶回过神,连跑好几步路,喊道:“大人,信是送给宁家的!”
付黄贺已经走出去很远很远了,念蝶不确定他听没听见,还想再喊一声,看到越来越远的男人冲她挥了一下手。
应该是听见了。
念蝶松一口气,怔然的站了片刻,转身朝凤罗宫走。
这一路上她心事重重,回去后实在拿不定主意,就找燕宁,将那个腰牌拿了出来,说了如何得到这块腰牌的前因后果,也把刚刚付黄贺握她手的事情说了。
念蝶正掏腰牌的手一顿,她心惊地看着面前突然变脸的男人,颤着唇道:“大人,奴婢怎么敢开罪大人,可这腰牌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