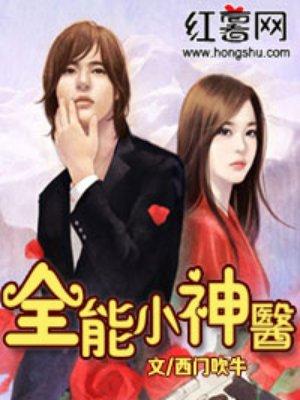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序列大明 > 第685章 真理狂想(第2页)
第685章 真理狂想(第2页)
「可陪伴嗣源四处游历的那几年,我现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,关心的依旧只是今日的饭菜是否可口,辛苦一个月的工钱何时能够结算,久病的家人怎麽样才能痊愈。」
「他们不会太过关心到底有谁最后成了仙佛,又是谁最后坐了天下。哪怕有人要抢走他们手中本就不多的东西,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反抗。最多揉揉泪眼,小声骂一骂,然后宽慰自己只要人还活着就好。」
张峰岳抬手揉了揉眉心,轻声道:「所以就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了吧。」
「老师,其实不止是这座帝国变了,就连您也变了。」刘谨勋忽然开口。
「有吗?难不成是越来越老了?」
刘谨勋没有理会老人故意为之的打趣调侃,神色依旧凝重。
「当年您在新东林书院担任山长之时,曾挥笔写下过一篇关于『大儒序』的策论,字字珠玑,读之令人心神振奋,热血沸腾。纵然儒序内部一直以来关于这篇策论褒贬不一,连您最看重的学生裴行俭更是对此嗤之以鼻,甚至不惜为此与您分道扬镳。」
张峰岳目光依旧温润如水:「不过只是一匹老骥偶的狂想罢了,做不得数」
「不,学生并未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狂想。相反我始终坚信这就是儒序最正确的未来!」
刘谨勋突然向后退了一步,拱手抱拳,对着老人躬身到底。
「那篇策论以『六艺』展为根基,以感教化育为核心,涵盖儒教学子身丶心丶理丶意四个方面,全文三千四百七十二字,学生至今依旧历历在目,不敢稍忘。」
刘谨勋头颅深深埋在持礼的双臂之中,话音却是激动昂扬。
「如此一篇旷古烁今的巨作,一现世便注定要成为新东林党的纲领,更是您日后成为儒家新圣的根基。学生大半生都在矢志不渝践行其中要义,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山野田间,从没有过半分懈怠。」
「可不知道何时,您却突然变了」
刘谨勋抬起身来,目光毫无躲闪,直视那双不再暗藏摄人锋芒,只剩下一片秋冬萧瑟荒凉的眼睛。
「我不明白是什麽原因,能让老师您将这份弥足珍贵的至宝弃如敝履,也将如我这样的追随者弃如敝履。」
刘谨勋语气变得哀怨:「我曾猜疑是不是因为裴行俭,因为我很明白,在您的眼中,只有他裴行俭才是唯一有资格能够继承您衣钵的传人。」
「不瞒您说,我很嫉妒,也因此而心生不满,甚至滋生出一丝攀比的妄念。所以我在返回金陵之后,暗中和朱家丶和春秋会往来。就是在等着或许能有一天,在您得知消息之后,也会亲自驾临刘阀,当面斥责我这个逆徒,质问我为什麽要背叛您。」
刘谨勋颤声道:「如此学生也能有机会再当面亲口问您,儒序的未来究竟将走向何处。若是能以死换得您回心转意,刘谨勋死而无憾。」
张峰岳嘴唇抿紧,原本半躺的身体已经坐正,盖在身上的披风不知何时已然滑落在地。
檐下滴落的雨水润湿了披风的边缘,却已经无人在意。
「可是我最终还是没能见到您。只等来了商家的法序,带给我两个选择,一条路是入番地戴罪立功,一条路是执迷不悟就地处决。」
走廊拐角处的阴影中,商司古环抱双臂,依靠着冰冷的墙壁,神情漠然看着这对容貌同样老迈的师与徒。
刘谨勋嘴角露出一丝苦笑:「我又告诉自己,应该是自己做的太幼稚,也太过火,犯下了这样无法饶恕的大错,所以您根本不屑再多跟我废话半句。心不甘,所以我不愿死,因此我选择了前往番地,全心全意推行新政。
「可学生我在番地看到的,却全是您要彻底绝天地通的决心,根本没有半分『大儒序』的影子。」
「老师」
刘谨勋双膝一弯,膝盖重重砸在布满潮湿水汽的地砖上。
「难道您真的要放弃『大儒序』?难道学生一生奉行追求的理念,真就只配一句狂想吗?」
刘谨勋的眼眸中充斥着不甘和希冀,还有几分深藏的恐惧,彼此交融,复杂难言。
他希望能够从张峰岳的口中得到真正答案,却又担心心中的幻想会在此彻底破灭。
「地上凉,先起来再说话。」
张峰岳眉头紧皱,嘴里说出的话音却还是十分轻柔。
可刘谨勋依旧执拗摇头,连声追问:「老师,您当真要放弃我们这群追随者,放弃您当年的梦想吗?」
站在远处的商司古虽然表面还维持着那副置身事外的淡然,可眼底却流露出一丝藏不住的急切,定定看着这边。
「那不是我的梦想。」
张峰岳沉默片刻,话音转冷:「我再说一次,那只是我闲极无聊之时的一次信马由缰的狂想,一次不切实际的虚谈!」
轰隆!
檐下话音落地,远空雷声轰鸣。
狂风骤雨之中,弥漫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息,似有一尊庞然巨物正在迫近。
「不会的,我毕生践行的理念怎麽可能会是不切实际的虚谈,我无法接受。您一定是被什麽人所蛊惑,所以才会做出绝天地通这样错误的选择」
颓然跪坐的人影传出呢喃的声音,犹如锋利的刀剑刺进老人的眼眶,搅得他目光颤抖。
张峰岳怒声喝道:「胡说八道!」
刘谨勋再抬起头,已经是泪流满面。
「老师,张希极已经快到了。是我向詹舜泄露了您的位置。」
尽管早有预料,可当张峰岳真正听到对方说出这句话,依旧痛苦的闭上了眼睛。
「老夫知道他张希极会来,可为何偏偏这个人会是你?」
老人长叹一声:「谨勋,你糊涂啊」
(本章完)